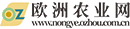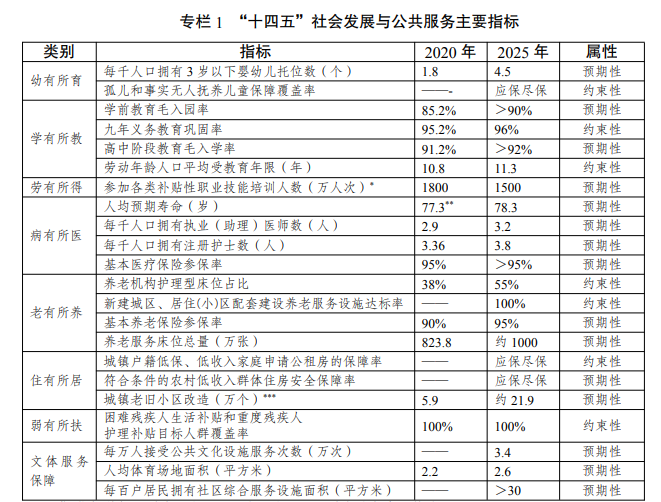退学重考后,人生道路会得到修正吗?
在一所985大学理工科专业读了三年后,孙睿决定退学,重读文科,24岁的他正在等待高考成绩。文图无关。 (视觉中国/图)
孙睿决定从那所985大学退学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想法在脑中盘桓已久。在读了一年大一和三年大二后,他再难忍受不断循环读大二的死结。2017年,他被一所西南名校的土木学院录取,很快感受到不适配。高中时,父母拒绝在他的文科选科表上签字,浸在理工科“简单符号间的复杂运算”中,孙睿时常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饥渴。
大一下学期,他陆续挂掉了包括大学物理、高等数学在内的一些通识类基础课。专业课也难以应对:他所在的专业要学工科里的10门力学,有些课程80%的内容要用到艰深的数理运算。
退学与勉力维持现状的天平,终于在一节流体力学的实验课上失衡。他看着同学们做实验,写报告,像在玩一堆数字游戏。他抄一抄就能过关,仍深觉自己像人群里一只不会爬树的猴子那样突兀。他说,解决困境通常遵循线性逻辑,困难越大,投入越多努力即可。可在那一刻,孙睿丧失了行动力。
他向辅导员和家长提出退学,遭到反对。按照学校的规定,本科生的最高修读年限是八年。他还剩四年时间去够一个学位,远未触及那条不得不退学的红线。辅导员提议,让他休学一段时间,调整状态。休学的三个月里,他背着书包,去了趟新疆,全程靠硬座和搭车、拼车的方式穷游,试着找回自己的行动力。开学后,他立马退了学。
理工科课业繁重。在大学,他曾抽空旁听过一些人文学科的课程。他说,那些课程就像橱窗里的商品,而自己像一名站在橱窗外的流浪汉,很羡慕,但无法购买。“(在大学里)时间本身在我看来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的,我感觉像是被迫完成一项表演性的工作,把这道题做了,获得了毕业,(就大功告成了)。”孙睿说。
如今24岁的孙睿正在等待自己的高考成绩。退学两年了,他改学了文科,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他想为人生设定的轨道。他不是没有分析过其中的利弊——远离高中的内容太久,难以考到曾经的分数;再读完四年大学,年龄上的劣势会远大于旁人。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
退学重考后,人生道路会得到修正吗?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多位退学重考的大学生和研究生,他们的回答有一个共同点:那或许是一次填补遗憾、纠偏人生的机会。
打开那个名为退学的开关
某艺术类院校毕业生郭语仍然记得五年前的那次退学谈话。那时,她还在北方一所铁路类院校读大一。她是浙江第一届新高考生,不分文理,擅长文科的她选了一门技术,因此可以填报部分理工科专业。志愿填报很大程度上被父亲的意志左右。父亲是铁路局的员工,为她挑选了一所铁路类院校的工程技术专业。
郭语更想读艺术类院校的编导专业。高三时,她无意间了解到编导,在兴趣之下兼报了艺术类。在没有艺考机构辅导的情况下,她顺利挺进华东一所艺术类院校的三试,但因为不熟悉考试内容和流程,以5分之差遗憾败北。
高三那个暑假,她曾犹豫是否复读,但想法很快被毕业季解脱、松散的氛围冲淡。“没有那个勇气,不敢作那个决定,我怕我会失败”。
大学最终以与期待相反的面目展开了。理工类课程令人头痛,她不清楚类似工程制图的课对她的人生能产生什么意义。在课堂上或课后,她读吴念真的散文、麦基的《故事》,以及一些讲编剧方法的书。铁路类院校规章严格,早上6点半必须起来晨跑,被子得叠成豆腐块,床单和被套要弄出棱角,地上不允许有一根头发,桌面不能有一个杂物。这和她散漫自由的天性相悖。
离开的念头在孕育。大一上学期结束,她又去了趟那所艺术院校“朝圣”。在校门口,一位女老师把她当成了本校学生,送给她一张奥德赛相关戏剧的票。她退掉了当晚的高铁票,在剧场看完那出戏,确认“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追求”。
她决定退学重考。最差的情况无非是考不上编导,再走一遍文化类录取。她说服母亲在退学文件上签字,两个人瞒着父亲,办理了退学手续。
退学谈话,班主任试图说服她:你都已经读了一个学期了,退学是在折腾,浪费时间。编导类专业以后工作不稳定,女孩子找一个安稳的工作比较好。
“我当时就觉得无法沟通。”郭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从北京一所211大学退学的张颐共享了类似的心路历程。
高考填志愿,张颐所在的省份,最多可以填96个志愿,以“专业+学校”顺序排列,按分数高低录取。她想优先选汉语言文学、戏剧文学和法学类专业。父亲没和她商量,擅自调换了两个志愿的顺序,她最后被北京某211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录取。她数学不好,学起来有些吃力。
对于不满意专业的大学生来说,解决困境主流途径有两种:转专业和跨专业读研。但两条路对张颐来说,都行不通。
她尝试换个专业,但被严格的转专业机制拦在门外。在那所211大学,转专业需要通过所在学院和意向转入学院的双重考核。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学院对转专业的明文规定是学分绩达到前30%,系里一共一百多号人,最后院里允许转出的只有三五个。再剔除掉没能通过意向学院笔试、面试的,只有一两个人能顺利转成。
而跨专业读研意味着,需要忍耐四年,才能争取一个换专业读研的机会。张颐拒绝漫长的等待。“我当时很迫切的一个想法是,尽快地学我自己想学的专业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如果继续等待,“这会让我觉得整个大学生涯都被浪费掉了。”
毕业季来临,部分学生却逆水行舟,选择重新高考或考研,试图修正人生方向。 (视觉中国/图)
领取一套新的人生剧本
对一部分人来说,退学重考确实能为自己的人生换取一套新剧本。
2021年9月,周施琳辞掉了一所建筑类企业的HR工作,到湖南一所综合类大学读研。入学的机会来自考研调剂,她原本考的是北方一所财经类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,但没过A区国家线。
学历膨胀的年代,周施琳一直对自己的本科学历不太自信。为了上岸,她付出了艰难的努力。从2021年7月起,她维持一种魔鬼作息: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,学习到7点50去上班,下午5点下班后,从晚上7点一直学到11点。午休时间也不放过。
调剂后的专业,和自己想报的专业在同一个一级学科下面。她起初感受到的是可以上学的喜悦。拿到课表、浏览完导师们的研究领域后,她发现两个专业的培养重点不尽相同。她想在人力资源领域深耕,但调剂后的专业更偏向于财会。
那不是她感兴趣的内容。她决定再考一次研。2023年,她踩线进了理想院校的理想专业。以前只有本科学历,“觉得没自信,自己处在山脚,当我考上,我会觉得我已经走在山的半途了。”她说,扛住压力退学重考,达成心仪目标,让她变得更自信了。
但并非所有退学重读的人,都能让人生如己所愿地驶入平顺的航道。
杨北辰在南方一所理工类大学读了四年材料学,很早就开始准备换专业读研。他所学的材料专业,因就业不好被戏称为“四大天坑”(生化环材,即生物工程、化学工程技术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材料科学与工程)。对于部分就业老大难的理工科学生来说,“转码”——转行写代码一度是一个热门选项。杨北辰记得,几年前,很多社交平台都弥漫着对计算机专业的狂热。“读一个计算机硕士,毕业年薪白菜价能拿20万-30万。”这激发了他对这个专业的热情。
第一次考研,他冲击华东某双非高校的计算机硕士,他发现,“竞争太激烈了”,没过复试分数线。最后兜兜转转,又调剂回了本校的材料学。他宽慰于,自己起码还能再上三年学,但仍然迷茫,“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”。如今再回顾,他说当年一头扎进考研战场,多少带点盲目,是被身边人一起拥着往前走。
一位从985院校退学的硕士生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种心态:“从小到大,大家一直处在一个竞争性的体系里,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好像把别人一个一个挤下去,自己才会获得胜利。大家会认为,从桥上掉到桥下的过程是非常可怕的,桥下就是万丈深渊的感觉。”
杨北辰起初自我暗示,好好度过研究生生涯,同时计划学一些编程知识。在他所在的大学,研究生的毕业要求还算宽松:发一篇二区SCI的论文,毕业再写一篇大论文。理工科研究生有科研任务,他的实验室日常重复而单调,不停地磨金相、抛光,“大量的技术性劳动”。
“可能我不太喜欢做科研。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研究出什么东西,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论文,然后毕业。”
他决计毕业后不从事本专业的工作,但又要泡在实验室里消磨时间,做的一切看上去都像无用功。“你不想学这个东西,不喜欢,还得非要学”。拧巴到了研二下学期,杨北辰决定退学,再考一年计算机硕士。
第二次考研依旧以失败告终。他跑去深圳找工作,互联网的运营、产品岗位,挨个投一圈。“折腾”的几年在他的简历上留下了痕迹。他面试过一家主营跨境电商的公司,对面是个四十多岁的女面试官,聊起退学经历,对方表示难以理解。结束后,面试官对他说:“如果不是因为你退学,我当场就把你录用了。”
“但我觉得退学这个决定我一点都不后悔,反而会很庆幸。”杨北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我觉得人的感受是很重要的,你不想要做的事,就可以不去做。”
坦然接受一切后果
“现在的年轻人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一种外在的进程和指标(推着走),支撑着所剩无几的个人意志。”孙睿说,退学后的第一年,他并未选择任何一个复读机构。他自认为看透了高考的本质,“没有任何生产性,把年轻人的精力和意志力消耗成一个可以供外界评价的数字。”他刚退学,“对复读非常排斥”。
他把那一年视为自我调整的gap year(间隔年)。他考虑过出国读书,但因为理想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,去境外留学并非良选。他也试着去应聘,但接受他的大多是一些销售岗。他转念,想着或许能做一做自由职业,报了网上的编剧班。效果难如人意。
靠速成的方式学写剧本,在市场上难以求得好结果,同时也很难让自己满意,最后发现,“无论求职还是自谋生路,都很困难”。受到现实的掣肘,孙睿发现“可能唯一的选择还是重新参加一次高考”。
只是这次,孙睿对大学的设想不是局限在一张文凭,而是想找到一个符合自己志趣的、能够充分发展的空间。
退学重考后,张颐从原来的211大学,“掉”到了现在这所双非院校。所幸专业是她想要的法学,对于现状她还算满意。很多人问过她,能否接受之中的落差。她摇摇头。她说,自己曾经迷恋那种标准化的升学路径:一路的985本、985硕,加上国外名校PHD,仿佛那才是人生标配。她曾经迷恋过名校光环,现在觉得,学历为因、能力为果的思维,实际上是一种逻辑倒置。
她的经历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很多人的问询。她发现,很多人都有退学重考的念头。有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,学小语种专业,想退学重新考法学,理由是小语种就业不甚乐观,而法学类专业日后薪资的天花板更高,能持久地缓解她的家庭经济困局。
一位从高一开始就立志学习法学的同学,报志愿时遭到父母反对,以为到了大学矛盾就能消弭。结果,内心对理想的偏执,让他难以继续学业。最后,他真的退学重考了。
在私信里,这位同学对张颐说:他能坦然接受复读的一切结果,这是一场对自己的救赎,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悔。
“会担忧退学重读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吗?”南方周末记者几乎问了所有受访者这个问题。
“像时间成本这种东西更多是外在的标准,站在社会的视角看自己,把自己的生命体验量化。但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的话,人生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起伏,即便是不太顺利的过程,也是宝贵的体验,这就是我的生活,我的人生本身,我的生命历程,不会觉得很可惜,只是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经历。”孙睿回答。
“我觉得眼光要放长远,不能只盯在当下这个阶段。我觉得很多人想要的结果一直都是自己刚开始想要的,但又一直把自己想要的结果后置,想着后面再说,但很多事情拖着拖着就没有了。”郭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这个毕业季,郭语刚刚从那所艺术类院校毕业。她现在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做编导,工作内容大致是用电影的思维拍短视频,对未来仍有一些迷茫。她说,这些迷茫都在合理的范畴之内,如果当初没有退学,自己或许会在铁路类单位做文员。她庆幸现在的选择,因为文员的迷茫,实在离自己想要的生活太远太远了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)
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